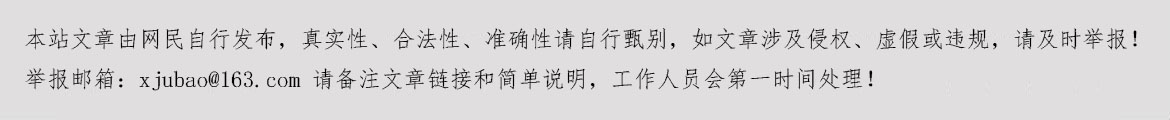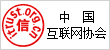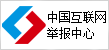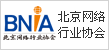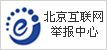唐山烧烤店事件,其实被打女子还是比较幸运的
2022-06-14 09:31:03
不少人看到这个标题,是不是想进来骂人了,其实大可不必,大家耐心看下去就知道有时候这种荒诞剧不是不存在,而是真实存在着。
大家在昆山龙哥反杀事件之前,可能从朴素的正义观出发,觉得人当然有反抗的权利,因反抗而失手将人反杀,既不具有道德内疚感,又有正当防卫的法律依据。
但是,为什么昆山龙哥反杀事件影响这么深远,那就是在昆山龙哥被反杀之前,大家的朴素正义观并未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成为一种广泛共识。
回到唐山烧烤店事件,我为什么说被打女子还是比较幸运的,她有三处幸运:
第一、这家烧烤店的摄像头竟然这么齐全,不但内部有,外部也有。
第二、这摄像头竟然一直没坏掉,而且清晰度亦不错。
第三、幸亏只是几个女子吃饭,同桌的没有男的,后面也没男朋友或者老公打个电话来问问夜宵吃的怎么样了,万一打个电话听到打斗声赶过来一起反打,那这事就又复杂了。
上面三个幸运,但凡有一个有点小插曲,这事都有可能往聚众斗殴去演化。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了,这世界还有没有王法了?难道女子被调戏在先,然后又是对方先动手的,这边如果有几个男的和女的一起反击对方,就变成聚众斗殴了?不属于正当防卫?不属于见义勇为?
虽然我觉得群众的朴素正义观很有道理,但在现实中还真有可能未必如此,下面是我亲身辩护的一个案子,案情其实很简单:
某年某月某日,A和B是先男女朋友关系,B和C是现男女关系,C知道了A和B竟然一起在酒吧,C通过B约A在酒吧附近的广场见面。A和B一起去C指定的广场见面,酒吧门口碰到A的同学D,告诉他C找他在广场见面,有点慌,D说和他一起过去。
然后,A到了广场,见到C已经带了一群人等在那了,见面后,C上来打了A三个巴掌,A没有任何还手,D看不过去,去推C和C的朋友,双方互相推搡直至打斗,D的朋友,也是酒吧员工E不久来到广场(E并不是A找来的),看到朋友在被打,就加入进去和对方打,最终E轻伤,而A(在各方笔录中均没人说A有打架,A自己在笔录中说当时他用手臂掐住C的脖子,但只是想拉开他不要打朋友D。)当天,因为E受伤,所以报警。
公安出警后以治安案件处理,参与打架的几人均行政拘留。但因为E受轻伤,就对C和C的朋友F以故意伤害罪立案侦查。大概过了10个月左右,却突然对A、D和E以涉嫌聚众斗殴罪立案。最后到检察院审查起诉时,A、D、E、C和F整案变为聚众斗殴,即认为属于互殴。
检察院审查阶段律师介入,认为不构成聚众斗殴罪,不符合聚众斗殴罪的犯罪构成。而且A、C、D作为学生,从起因上仅为感情纠纷的情况下,也不应以聚众斗殴罪进行追究。
但检察院不予采纳,要求A认罪认罚给缓刑,她准备马上起诉。这个案件当时其余四人已经全部认罪认罚并接受了缓刑的结果。
但我还是认为不构成犯罪,不应起诉,否则对A不公平。并且和公诉人沟通:这个案件对于你和我而言,都只是一个案件,只是一份工作,但是对于A而言,却是一个人生。
经过多次沟通,又提交补充辩护意见书。公诉人还是坚持构成聚众斗殴罪,只是暗示在构成犯罪的前提下,不予起诉也是一个选项。
最后,这个案件整案不予起诉。
有人可能会说你为什么坚持认为无罪的情况下最后同意了认罪不予起诉的选项,这种艰难抉择大家可以看我的另一篇公号文章《认罪认罚下的辩护博弈》。
这个结果,虽然同样没有犯罪记录,A也接受了这个现实。但是这个案子,从法律上其实值得我们深思,至少我觉得不符合我内心朴素的正义观。下面附上当时的第一次辩护意见,第二次辩护意见因涉及不少证据分析,就不再展示。
司法机关的逻辑超越了理性之理性,认为:那种场景下你为什么不报警,不等警察来处理,你被打了三巴掌,你的朋友不应该帮你出头,应该报警,你朋友被打了,你不应该亲自上去拆架,应该报警等着公安来,在这期间你朋友被打那只能被打了,这种逻辑是非常可怕的,让正义得不到伸张,让邪恶可以横行。
法律不应强人所难,不应过于冰冷而无情感,理性之上有情与理的交融,如此方才是有血有肉之人。法律应当鼓励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催生冰冷的冷血动物。
犯罪嫌疑人A被指涉嫌聚众斗殴罪一案
之辩护意见书
本人受犯罪嫌疑人A的委托,受**事务所的指派,在贵院正在审查起诉的A等五人涉嫌聚众斗殴罪一案中担任涉嫌聚众斗殴罪的犯罪嫌疑人A的辩护人。辩护人在查阅了本案全部书面案卷材料及起诉意见书和对A的询问,结合相关法律和事实,特向贵院发表如下辩护意见,望贵院予以采纳:
一、从纠纷起因看,本案不应按聚众斗殴罪进行处理
第一、从各犯罪嫌疑人供述、以及证人B(女)等人的陈述可以看到C等人与A等人的冲突系因C、A、B三人之间的感情纠纷所引起的,而案发时C、A、B均还是在校就读的学生(大专生),案件起因亦被**诉字**号《起诉意见书》所认定。
第二、依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聚众斗殴犯罪案件相关问题的纪要》(下称《省高院会议纪要》)第一条规定:聚众斗殴罪是1997年刑法修正案从流氓罪分拆而来,聚众斗殴犯罪不仅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而且严重侵害公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由于本罪“聚众”的特点,参与人员多,危害性大,打击的重点是涉黑涉恶、护黄护赌护毒引发的双方或者多方群殴行为。对于因建房、土地权属、用水等民间纠纷引发的双方多人斗殴,中学生或者未成年人之间因为普通矛盾引发的群架,一般不按聚众斗殴对待,但是雇用打手或者纠集闲散人员斗殴的,应以聚众斗殴论处。
第三、结合《省高院会议纪要》的规定,本案系三人之间的感情纠纷而起,并且均系在校学生,且参与人数本身亦不多,而且后续参加的D、E系不属于A雇佣的打手或者纠集的闲散人员,D系A的在校同学、E是**酒吧的员工,而且E亦非A召集而来。
第四、本案案发时间为2020年10月4日凌晨,案发后E与F之间也已达成和解。而A本人则也已受到行政处罚,**行罚决字**号认定A系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被行政拘留三日。因此,其行为已经受到了与其过错相当的惩罚。
综上,辩护人认为本案仅仅系感情原因所引发的民间纠纷,从A本人而言,并不存在要主动去实施打架斗殴、扰乱社会秩序等流氓行为的主观故意。本案对A不应按聚众斗殴罪进行处理,其行为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希望贵院能给A一个机会,否则背负着刑责,对其将来能否顺利毕业,毕业后走入社会亦是一个重大的障碍。
二、从犯罪构成看,本案A亦不构成聚众斗殴罪
(一)A并不具有聚众斗殴的主观故意
首先,B于2020年10月4日案发当天在**派出所作出的询问笔录(诉讼证据卷标页297)陈述:2020年10月4日凌晨我与朋友在**酒吧玩时,我的男友C发短信给我,让我把A约出来谈一谈,到凌晨2:50时左右样子我叫了A,路上遇到了D一起来到**西侧小广场与C、F及其他几个人见面……”这与A、D的供述是能印证的,即系C提出找A谈一谈这个与B有关的事,并且D也是路上偶然碰到一起,并非有意召集人前往斗殴。
其次,不论是C等人的供述、证言,还是A等人的供述、B的证言,均充分说明了当时A在与C碰面时,出手打人的是C,A在C向其连续扇耳光时并未还手,也并未叫其他人还手。若A当时系前往**小广场进行聚众斗殴,则不可能在C连续扇其耳光时不进行还手,或招呼人进行还手。至于D、E与C等人发生冲突,并非系A招呼下所为,系为了避免A被打的一种正当防卫,且强度亦未超出限度。
最后,从D、E、G等人的供述里,亦清楚地可以看到A并未纠集E、G等人前来。
因此,A自始至终不具有聚众斗殴的主观故意,后续发展成群殴系非其所愿和能受其控制。
(二)A并无聚众以及斗殴的客观行为
本案中虽然公安认定A一方有三人即:A、D、E参与斗殴,但事实上,无论从D还是E的供述里,可以发现E的出现并非系由A召集而来,其本身并不知道E会出现。聚众斗殴一般是指双方各纠集三人以上进行斗殴的行为,显然本案中A并不存在纠结三人以上进行斗殴的客观行为。
结合本案C一方和A一方的供述以及证人证言,均未有人指认A参与了斗殴,相反是A在2020年10月4日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据卷标页279)中陈述:“……C和他身着绿色上衣的朋友(F)一起冲过去把D往草丛里推,我看到D被打,我也冲过去了,先抱着C的肚子,然后用手臂卡住C的脖子,叫他停止打D……。”这在后续的询问笔录、讯问笔录中均是如此表述。可见,当时A唯一的出手只为了叫C停止打D。他的这种行为其实并未超出普通人员的思维逻辑,包括我们辩护人在内的法律工作人员不能冰冷的认为此时不应该上前阻止C的打架,应该第一时间报警,等警察来处理,可这显然不符合正常思维,当一个维护自己的朋友被摁在地上打,而自己不第一时间上去阻止却冷静的报警,辩护人认为这即使是法律工作者在那种场景下都不一定能让自己如此冷静。法律不应强人所难,而应考虑他们系18岁左右血气方刚的年纪该有的判断能力。
因此,A并无聚众的行为,亦无斗殴的故意和行为,辩护人恳请贵院对此作出认真审查,以防止扩大化处理。不能为了对等性,在E被C、F故意伤害形成轻伤的情况下,为追究C、F构成故意伤害罪,而扩大化地追究A的聚众斗殴罪,却无视相关《省高院会议纪要》规定和聚众斗殴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以及案件的客观事实。
(三)A亦非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不符合追究聚众斗殴罪的主体要件
《刑法》第292条规定,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刑法》第97条规定,本法所称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聚众斗殴犯罪案件相关问题的纪要》第三条第三款亦规定,为主纠结人员,或者在斗殴时负责组织、指挥的,应认定为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结合本案证据以及如前所述,A前往案发现场并非由其发起,而系听到B转述的C要求谈一谈的要求下前往。并且D也是路上偶然碰到聊起C的事情而前往,后续的E、G等人的出现均非A所组织,包括后续斗殴的起始和过程、结束亦不受A的控制和指挥。包括D、E两人的供述均清楚地可以发现系他们看到A被C连续打巴掌,才主动与C进行冲突,并非受A指令,相反A还试图拆架。因此,A显然不属于所谓的首要分子。
依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聚众斗殴犯罪案件相关问题的纪要》第三条第四款规定,纠集多人斗殴的,提供斗殴凶器的,接送多人赶赴、离开斗殴现场的,在斗殴时行为积极的,一般应认定为聚众斗殴的积极参加者。结合案件事实,A显然不属于积极参加者,本案中只能说案件起因是因A的感情纠纷而起,但并不能说本案系A在发挥主要作用,这是有本质区别。A自身被C连续扇三巴掌而未还手,除了在D被C等人摁在地上打的时候,为了拆架而用手肘抱住C脖子,想把他从打D的身上拉开,其他再无与斗殴有关的积极主动的行为,E等人亦非A纠集而来,亦不存在提供凶器和接送多人赶赴、离开斗殴现场的积极表现。这从公安向各犯罪嫌疑人以及证人讯问、询问中亦可得到印证。因此,A绝非积极参加者。
因此,退一步讲,即使本案中存在聚众斗殴的行为,但A既非首要分子亦非积极参加者,亦不符合聚众斗殴罪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主体要件。
综上所述,本案A并不构成聚众斗殴罪,请求贵院审查后不予起诉。